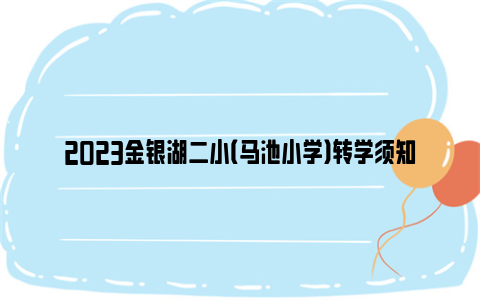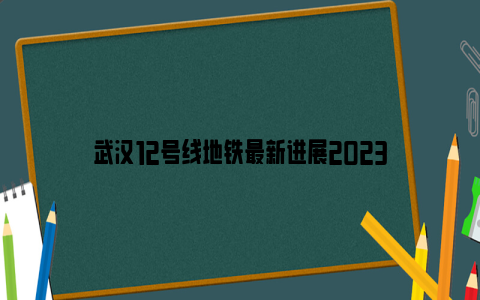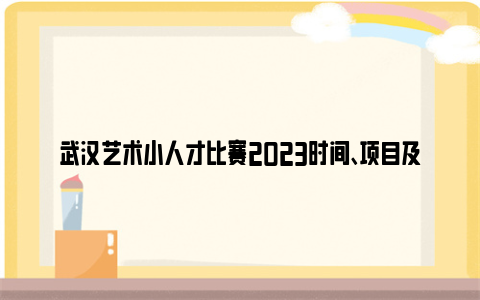王钢,1982年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中文系,后进入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历任湖北省志总编室编辑、副主任,综合处副处长,资料研究室副主任,年鉴工作处处长,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巡视员、《湖北年鉴》副主编、湖北省年鉴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出版协会年鉴研究会常务理事。
各位方志、年鉴同仁,大家下午好!非常有幸参加武汉市志办的方志讲堂活动,对我来说这是个宝贵的学习机会。
来到市方志办,一个感受是非常熟悉和亲切。因为我出生于汉口,是一个地道的老汉口人,市方志办所处的大智路一带有我的母校黄石路小学,还有现在的警予中学,这里有我许多青少年时代难忘的记忆。每次到汉口,仿佛是回家乡寻找乡愁。另一个感受就是市方志办举办方志讲堂的这种方式非常好。地方志是一项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工作,需要经常进行切磋交流,形成一个良好的理论研究、业务钻研的氛围。我相信,通过方志讲堂能够进一步提高地方志工作者在方志年鉴工作方面的业务素质,更好地完成修志编鉴的工作任务。
在交流年鉴业务知识之前,我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年鉴工作的一些信息。全国第五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以来,尤其是2015年国务院颁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来,全国地方志工作高位运行,作出一系列新的工作部署。今年7月中旬,我参加中指组召开的全国年鉴会议,会议内容一是年鉴精品工程的部署;二是举行全国年鉴的评奖活动。湖北省有15家参评单位,经过全国专家的评比,有9家单位得到表扬。其中值得欣喜的是,《武汉年鉴》荣获特等奖,还有《汉阳年鉴》《襄阳年鉴》《夷陵年鉴》《武当山年鉴》《长江年鉴》等年鉴都获得表扬,这是湖北省年鉴界的荣誉。7月底,中指办在新疆召开“两全”目标工作推进会,李培林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聚焦主业,履职尽责,用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刻认识按时保质地完成“两全目标”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据会议精神,湖北省在本月下旬即将召开“两全目标”工作推进会。8月,我又代表湖北省参加了在齐齐哈尔和通辽召开的全国年鉴会议。中指办主任在会上指出,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全国地方志系统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历史文化创举,也就是自古以来只有我们这一代方志人才可以实现省省有志鉴、县县有志鉴。从世界范围看,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这样。方志文化应该走在世界文化舞台的中央,当前工作的重点就是要推进年鉴的全覆盖。目前,湖北的年鉴全覆盖任务已完成99%,走在全国的第一方阵。但把一年一鉴和公开出版这两项要求加上后,湖北在全国就只能排19位。尤其是在公开出版方面,湖北目前只有46%。根据中指组的要求,省方志办正在着力推进全省地方综合年鉴的全覆盖、一年一鉴和公开出版,重点是后面这两个方面的工作。而这三个方面,武汉市都走在全省的前列,带了好头。武汉市的经验,下一步要向全省推广。争取能够在“十三五”期间,全省年鉴工作尤其是在公开出版上要迎头赶上。
今天方志讲堂的题目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年鉴和志书不同,年鉴是舶来品,作为年鉴工作者,有必要了解年鉴的起源,了解国外年鉴学术发展的动态,与国内的年鉴做一些比较研究,学习借鉴国外年鉴编辑出版的经验,从而推动我国年鉴编纂与研究的繁荣发展。
一、年鉴的起源与发展
年鉴起源于西方。从时间轴来看,年鉴出现于12、13世纪,14世纪逐渐标准化,并在16、17世纪获得发展,18世纪早期开始形成现代的年鉴,到18世纪中晚期定型。从空间分布来看,年鉴随着西方文明中心的转移而扩展。西方文明最早受到阿拉伯文明的影响,再往后是古罗马、古希腊,后扩展到欧洲大陆。英国工业革命后,英国发展比较快,其后西方整个文明的中心又往美洲转移。基本上年鉴的起源与发展也体现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
据学者考证,年鉴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历书。在各类书籍中,历书是起源最早的典籍之一。古代人观察天象,记载天文变化,形成历书。天文学是最古老的一门学科。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主要从天文现象的观察研究开始。日出日落,潮起潮落,四季更替,年复一年,对大自然变化的观察,给人类带来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最直观的感受,也不断加深了人类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认识。毛泽东同志说过: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科学。这个认识过程在西方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古人对大自然模糊的认识,能够解释就解释,解释不了时就产生了宗教。宗教在早期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很高,古代的历书和宗教关系密切,历书记载的内容还包括国家庆典,农业社会的四时祭祀等。古代的历书尽管还不是科学,但已经形成以客观记事为主的基本属性。这种属性对年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学者研究,到希腊罗马时期,有一些被认作是古年鉴的作品,就吸收了历书的特点。古希腊时期的古年鉴,与记录行星和其他天体的天体星体图有关。除了对天文的记载外,还逐渐增加宗教、民众和社会活动的内容,其记述范围更广,包括对地方官吏的任命、每天发生的事务、行政管理等,都记录了下来。这和中国古代的实录有些相似。
到了中世纪以后,欧洲开始海外扩张,随之带来殖民主义的发展,而向海外扩张迫切需要的就是与航海有关的技术和知识。现代科技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其中一点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内陆型国家,地域辽阔;而西方由于地域狭小,有领土扩张的需要。对天文知识和航海技术的需求,间接带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欧洲文明就在环地中海的地理环境中产生。这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理解年鉴起源于西方是与西方文明的发展相适应的。
欧洲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经过了14到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迎来17世纪早期的英国资本主义革命,以及伴随而来的西方工业革命,由此带来整个欧洲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文化的繁荣。新的知识、新的技术不断地为年鉴的普及和进一步定型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社会需求。其中印刷术的发明对年鉴具有重大意义。以前的古历书、古年鉴有很多是羊皮书和手抄本,现在有的地方还保存着这些珍贵的书籍。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年鉴变得更普及,发展得更加完善,逐渐成为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一种知识性、工具性的书籍。
马克思说,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向世界范围的扩展,很多欧洲移民到新大陆淘金,于是把年鉴也带到了美洲大陆。年鉴的发展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美洲。美国在17世纪编出第一本年鉴,名为《1639年新英格兰年鉴》。据说当时很多人家里只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还有一本书就是年鉴。说明当时年鉴的社会需求度很高。后来比较有影响的年鉴有《罗德岛年鉴》《穷查理年鉴》等等。
西方年鉴的类型、数量比较多。据1923年出版的《1700种年鉴分类指南》介绍,西方年鉴书约有1700多种,包括各种年刊、名录、年鉴、工具书等,由此可以反映英美年鉴的发展已经达到比较繁荣的状况。
根据现在学术界的研究,西方年鉴主要有三类,一类是Almanac,一类是Year book,一类是Annual,这三个英文词都代表年鉴。大致可以这样理解:Almanac对应历书,Yearbook对应年刊、年书,Annual对应的是编年史。应该说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年鉴的源头,它们既有共性,又有所区别。
第一类Almanac,目前使用得最多,学者一般认为它是来自中世纪阿拉伯语,由古历书演变而来。16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年鉴使用这个名字,到17世纪逐渐成为在英国最畅销的书籍。英国每年能出版40多万册Almanac,代表作有《罗宾年鉴》《老摩尔年鉴》《航海天文年鉴》《土地测量员的天文年鉴》《航空铁路年鉴》《老农夫年鉴》等。英国比较有名的《惠特克年鉴》,被称为英国最好的年鉴和第一部微型百科全书,收录的内容包括各国的基本情况和各个学科的科学知识,以及英联邦的统计资料。美国最著名的年鉴是《世界年鉴》。
第二类Yearbook,这个词在中国用得比较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创办年鉴以来,很多年鉴书名的英文翻译大多采用这个名词。国内有学者研究,Yearbook起源于英国法庭上的案件提要或者是目录,法庭每年办的案子很多,所以就每年汇编一本。到18世纪初,Yearbook这个词才有了现代年鉴的含义,逐渐演变成对各个方面的大事进行年度统计汇编的资料书籍,其工具书的功能得以扩展。目前国外用Yearbook这种形式编的多半是专业年鉴。
第三类Annual,词义是一年生的植物,年度性的东西。也有人把它理解为年报、年刊、编年史。这类的年鉴也不少,如英国的《世界大事件年鉴》,美国的《参考书年鉴》《外科年鉴》,等等。《世界大事件年鉴》的记事方式是以文章形式为主,向读者展示过去一年的各种情况、大事件、发展趋势,很多条目文章都是专家撰写,比一般的参考书更深奥一些,后来这部年鉴改由美国出版。
还有一种Factbook,如美国的《农业年鉴》(Agricultural Factbook)、《中情局世界信息年鉴》《文化人物年鉴》《人物年鉴》,等等。一些工具书,虽然不叫年鉴,但每年出一本,其实也是一种年鉴,在西方的分类上把它归入工具书、参考书。
由此可见,年鉴起源于西方,它有多个源头,经历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适应人们对事实资料的需要,逐渐演变形成现代的西方年鉴,并且还在呈多样性趋势向前发展,是以年度为时间维度,以地域、学科、专业的变化情况等为空间维度的一种书籍样式。
二、中国年鉴事业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世界几大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是几千年来没有中断的,尤其是在历史记载方面,中国历史文化悠久灿烂。最近学界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印度的比较,新加坡学者有一篇文章,研究印度能不能超越中国,结论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印度没有中国这种文化基因。印度历史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很长时间没有形成自己统一的文化,历史文化记载也不如中国丰富,而且印度的语言文字到今天仍不统一。印度曾经是佛教的发源地,但是关于印度佛教的历史记载几乎完全消失,研究这些历史要到中国的历史和佛教典籍里面来找。印度的历史从来就不完整,这一点和中国有很大的差异。而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差异其实与文化的差异有着密切关联。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文献编纂传统的国家,可以说中国历史文化一点也不逊于西方国家。中国很多历史典籍和年鉴有渊源,像历书、辞书、类书,都具有百科全书的某些特性。与年鉴相似的,还有中国的方志。
现代形式的年鉴,是伴随着西方列强入侵及西学东渐,从海外传入中国的。从清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年鉴开始了草创时期。开始是外国人创办的年鉴年刊,如英国人编的《进出口贸易统计年册》,主要反映海关贸易的年度状况,内容非常丰富,是研究中国近代贸易史非常重要的资料,也可看作是中国现代年鉴的开先河之作。《新译世界统计年鉴》是中国第一部完全取材于国外的年鉴,它翻译了大量的内容,包括西方的文明、制度、概况等等,对西方文明的传入发挥了重要作用。编于1912年的《世界年鉴》是中国人自己编纂出版的第一部具有现代性质的年鉴,在中国年鉴的编纂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年鉴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年鉴种类数量增多。1924年出版的《中国年鉴》,对各行各业的情况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到20世纪30年代,年鉴编纂出版出现一个小高潮,出现了短暂的年鉴热。这个时期年鉴的特点一个是数量种类比较多,有学者统计总数达280种之多。有地方性年鉴,如广东、江西、江苏等地都有年鉴出版;有专业性年鉴,如广州《商业年鉴》《商场年鉴》《工商年鉴》等。第二个特点是存续时间比较短。民国初建,军阀割据,战乱频繁,加上后来日寇入侵,人力物力财力都受到限制,80%以上的年鉴都是昙花一现。第三个特点是文献资料非常珍贵,记载了清末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尽管很多年鉴只出版了一两年便遭中断,不够完整,但仍留下十分珍贵的资料,对那一时期的历史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后,年鉴编纂出版有了新的发展。《开国年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综合性年鉴,记述了新中国各方面的成就。还有其他一些专业年鉴,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年鉴,但品种不多。1949年到1965年期间,据统计只有12种年鉴出版,这和作为有几亿人口的大国是极不相称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年鉴事业都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各行各业对国家、地区发展情况和行业、学科信息的需求陡增,同时也受到全国范围编修地方志热潮的推动,年鉴开始受到社会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年鉴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80年《中国百科年鉴》编纂的出版,带动了各行各业年鉴创办。地方综合年鉴异军突起。1983年全国第一部地方综合年鉴《苏州年鉴》创刊,1984年第一部省级年鉴《河南年鉴》创刊;还有1985年《武汉年鉴》创刊,成为湖北省第一部地方综合年鉴。尤其是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以后,地方综合年鉴一跃成为年鉴业的主体。据统计,全国的年鉴现在已经达到5000多种,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年鉴数量最多的国家,是名副其实的年鉴大国。这与西方现在年鉴的数量不断减少、年鉴事业逐渐萎缩形成一个对照。
三、中外年鉴的特点,比较及启示
比较中外年鉴,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和不同点。最主要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性质相近,都是具有资料性的工具书。其次是记述内容相近,都是记述上一年度发展变化的情况;编纂出版的方式类似,都是逐年编纂,连续出版。再就是年鉴编纂出版时间类似,国外年鉴一般也是在下半年出版,说明编纂出版年鉴有共同的工作规律。
不同点,第一是编纂主体有所不同。中国的年鉴编纂主体主要是官方,年鉴的主编从业者基本上都是行政(事业)单位人员。而国外年鉴多是由出版公司、报社或研究机构编纂出版,甚至还有个人编的。美国的《世界年鉴》编辑部只有几个人,运行着一个庞大的编辑网络。第二是功能定位不同,内容各有侧重。中国的年鉴,由于大多是官方主办,性质是官书,编纂年鉴是官职官责。《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综合年鉴归属为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是方志和年鉴共有的功能,年鉴与方志渐渐具有趋同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年鉴继承了重史的传统,偏重于记述功能,更有编年史的性质。国内年鉴主要面向机关单位、机构部门,而国外的年鉴更体现大众色彩,是面向大众的工具书,更具实用性,所以它的特点是杂、博、碎。如美国的《世界年鉴》,提供的资料信息量非常大,每年都要加入大量的新信息,都是读者需要的东西。作为一种工具书,每年编,每年变化,每年更新。《华盛顿州年鉴》收录了大量姓名、地址、传真、政府机构名称电话等,为大众提供信息服务。国外年鉴重实用,重现实,对未来很感兴趣,有种探索精神,有的年鉴甚至还收录预测未来的信息。第三是服务对象和服务领域不同。中国的年鉴重视资政功能,国外年鉴突出实用性,读者面广,社会各界、各行各业都可以使用它。第四是年鉴的印装方式、定价和发行量差异也比较大。国内年鉴都是16开本,这是业界的规定,多为精装,且有越来越追求豪华的趋势,但发行量都不大。现在不少年鉴已经不考虑发行量了,改为赠送。市县级年鉴印数越来越少。相比之下,国外年鉴售价则比较便宜,用小开本,单色印刷,发行量大,读者覆盖面广。第五是年鉴读者的查阅率和利用率差别大。还是拿《世界年鉴》举例,其发行量很大,社会普及率高,各行各业包括研究人员、商人、学生、老百姓都乐于使用。国内年鉴由于发行量不大,在图书市场占有率不高,难以普及,读者查阅检索比较少。国家图书馆专家曾经介绍,他们在馆内专门设立年鉴阅览室,将收藏的大量全国各地的各类年鉴供读者查阅,但读者寥寥,是读者查阅率最少的一个阅览室。去年我在开全国省级年鉴研讨会的时候了解到,中国知网发布过一个关于全国年鉴检索数据的报告,对全国31部省级地方综合年鉴和15部副省级综合年鉴,还有18部北京的县区综合年鉴,做了一个读者引证频率的分析,相当多的年鉴就是几十次,几次,甚至还有零次。说明年鉴普遍存在检索率不高、社会利用率太低的问题。中国知网的报告里面还提到,对地方综合年鉴的查询远远低于对地方统计年鉴的查询,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查地方综合年鉴十次,查统计年鉴就是近百次。这就对编辑出版地方综合年鉴工作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编好年鉴,如何提高年鉴的利用率?一部年鉴,花这么大力气编出来,占用了国家和社会的资源,还有众多作者编辑辛勤的劳作,但它却没有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被束之高阁,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值得年鉴工作者深思。
最后谈一下对年鉴工作发展的几点思考。目前年鉴编纂出版工作还存在一些共性问题:一是地方综合年鉴(包括专业年鉴)同质化的现象明显,千鉴一面,没有自己的特色,年鉴的体例框架设计也趋同,明显缺乏个性。二是年鉴内容的重复很严重。我看到一篇论文里提到,有一本直辖市年鉴里,50%的资料内容在该市其他的各个专业年鉴(如该市的教育年鉴、科技年鉴)里面都可以找到,而且内容重复的比例还在不断提高。第三是年鉴事业的创新发展,这是一个提了十几年的老问题。怎么创新?年鉴事业如何健康、科学地发展?今天看来,尽管年鉴的数量在增多,覆盖面在扩大,政府拿出众多的财力,人力物力也都得到一定的保障,工作条件比以前大有改观,但年鉴受社会的关注度却在下降。这条路走下去,年鉴还能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能否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生存下去?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索和思考。我的看法是,年鉴如果不改革,编纂出版者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如果不改变,年鉴将来的路或许会越走越窄。第四是适当地去行政化问题。地方综合年鉴代表官方,完全没有行政色彩不太现实,但是要不要适当地去行政化?是否应该针对读者需要适当增加年鉴的趣味性、知识性、工具书属性?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社会上那么多的热点、亮点,读者关注的新东西、新事物,但是由于我们的观念被束缚了,很难去把它们纳入到年鉴中。譬如年度的新词、热词,那些被读者关心的一些新知识、新内容,年鉴框架中没有设计栏目去容纳。年鉴从业者们应该积极探索。第五是年鉴的效益问题,在重视社会效益的同时,还要不要考虑经济效益?要不要适当引入市场化运作模式?目前这样长期依靠政府财政,年鉴出版后全部送出去,财政投入一分钱也不需要收回来的模式是不是长期能够得到保障?会不会出现财政经费收紧,工作难以为继的时候?是否符合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年鉴事业发展方向?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思考研究。还有年鉴的宣传普及不够,年鉴的低使用率,以及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不断涌现,竞争激烈,信息密集、大数据广泛影响生产生活方式的新形势下年鉴业究竟应如何生存发展,这都是需要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总之,中外年鉴在基本属性上大体相同,但是因为国情、体制、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不同,中外年鉴在编辑目的、功能定位、服务手段、覆盖范围和利用率等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比较这些异同,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借鉴。发达国家现在已经跨过工业化时代,国外年鉴的生存条件和发展基础发生较大变化,正由纸质年鉴向网络年鉴方向发展。当前我国尚处在工业化时期,纸质年鉴方兴未艾,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在互联网时代,年鉴怎样做到既保持官书官媒的基本属性,又能增强一些工具书和实用书籍的特色,适应时代的需要,更好地服务读者、服务社会,这就需要了解国外年鉴的发展历史和发展现状,结合中国的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年鉴的创新之路,完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年鉴大国向年鉴强国转变的历史使命。
原创文章,作者:nbdnews,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nbdnews.cn/01/14/35/283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