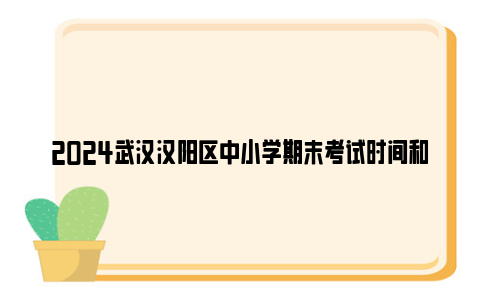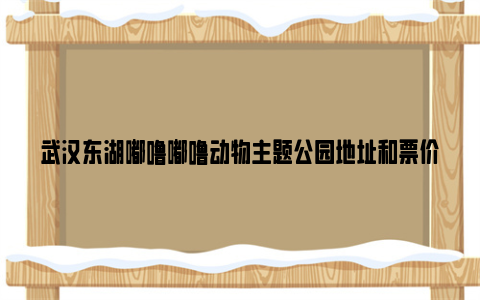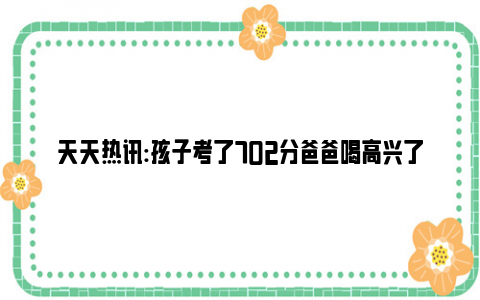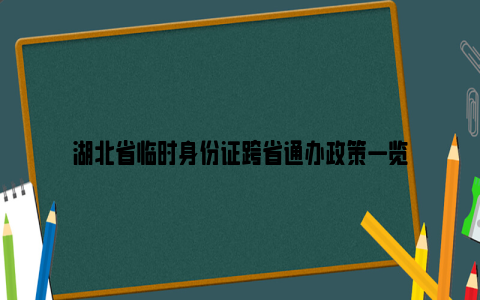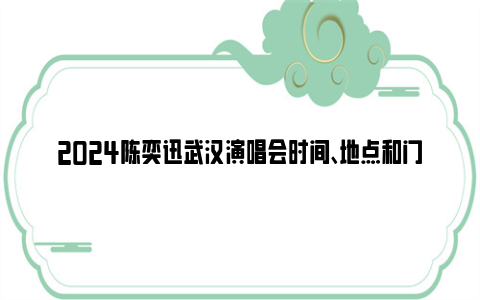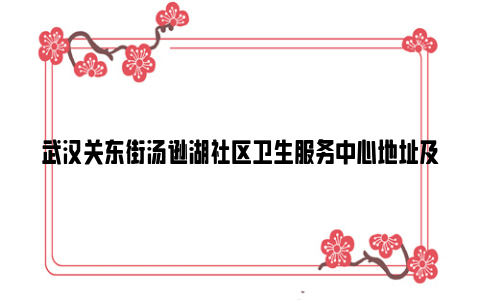我祖籍黄陂东乡,出生于武昌的仁济医院。
武汉自古就是九省通衢之地,交通方便,当然信息也就灵通,这是后天赋予人聪明;又是鱼米之乡,这是先天赋予人聪明,武汉人当然也就更加聪明,脑筋活泛,堪称“九头鸟”的代表。鸦片战争以后,海禁开放,西学入境,武汉也是得风气之先。我祖父涂介庵先生是清光绪年间的翰林。日、俄战争后的1905年底,他在直隶(今河北省)钜鹿县知县任上,请求赴东邻日本考察。获批准,于次年农历三月下旬启程。在日本,他日程安排得很紧,实地看了其新兴的工农业、交通、邮电、商业、税收、医药卫生、各类学校教育、政权管理、法院、监狱等方方面面,费时两个多月;归来写成数万字的《东瀛见知录》一书,详细记述了日本人学西方,如何以人为本,学其民主、法治精神,及科学的管理、先进的技术等,学得很彻底。而反观国人,则往往学其皮毛,很不成功。书的结尾,祖父感慨系之地说:“维新时代万绪千端……除改良政体,普及教育外,固无本末缓急之可言。”这些将近一个世纪前讲的话,今天读来仍新鲜如昨。
在祖父开明思想影响下,20年代,我的叔辈先后有4人赴美国留学,分别获政治学、农学、水利、土木工程的博士,学成回国,为国家、人民效劳。我的姑辈,都没有缠足,最起码都受了中等教育。至于今天祖父的孙辈、重孙辈男女,则大学生、洋博士更不在少数,超过了我的同辈和父辈。
我出生于国难深重的1933年。我从记事时起,在大武汉,我的思想一点儿都不闭塞。早年我听母亲说过,那些为母亲接生的信教的“白衣天使”,待母亲特别和善,使我小时候对信耶稣教的人,既好奇,又有亲近感。80年代初,我回武昌时,一位朋友还陪我去看了仁济医院的旧址。童年对我熏陶最深的是那些唱遍城乡的抗日歌曲,像“卢沟桥”、“长城谣”、悲壮的“流亡三部曲”,还有“热血”歌(“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的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出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我们的热血!……”)这些歌曲,我至今仍能哼唱,它铸就了我们一代人对外反帝、对内反封建专制的爱国情怀。抗战胜利后,我是武昌的一个中学生。在实验中学,老师们都很敬业。国文老师讲的故土楚国诗人屈原的形象和他的楚辞,深入人心。使我们懂得了人格的美。要学着终生做个为民为国的正直的人。武昌胡林翼路(现民主路)是一条书店街,课余,我在书海广泛涉猎。茅盾、巴金的长篇小说读遍,胡适、林语堂的文章,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钱钟书的《围城》,是在这里读的。常读的杂志有上海出版的《观察》、《时与文》、《中学生》、《文艺复兴》和《文艺春秋》等。鲁迅、茅盾的作品,苏联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使我思想左倾化,也迷上了文学。想做个进步作家的愿望,此时萌生了。我尝试向武汉的报刊投稿。我的第一篇练笔的短小说《何达静先生》,就是1949年春天在武汉的《和平日报》副刊发表的,这也是我平生头一回收到稿酬,那年16岁,高二的学生。
在武汉,从1946年开始的反内战,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争民主、争自由的学生运动,我虽没有参加,但很关注。国民党军警进入武汉大学校园,用达姆弹枪杀学生的“六一”惨案,给我印象很深,我曾去现场凭吊,也点燃了我心中争取民主、自由之火。在中学校内,我曾张贴壁报,向校方管制学生思想的倾向开火。
1949年8月1日,我进入中共中央中南局主办的中原大学政治学院第四十七队学习,从此开始了我全新的钻研马列主义和集体化的生活。4个月结业后,我又考入文艺学院创作组,学习解放区的新文艺。一年后我进人汉口黄陂路的中南文联,开始学做一名文学编辑,两年后调北京,仍是做文学编辑,这成为我大半生的职业。可是离休后,我可以做个自由的专业作者了。
武汉,是生我、养我,我成长之地,这里“天际流”的浩浩长江、这里自由无羁的先祖楚国的文化,这里的大气度和开放,对四方八面,各种优良文化的兼收并蓄,是我生命中永不衰竭的泉流,也是我的信奉和皈依。
(作者67岁,黄陂人。中国作协会员。曾任《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达20余年。离休前任《传记文学》主编,编审)
原创文章,作者:nbdnews,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nbdnews.cn/07/16/27/294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