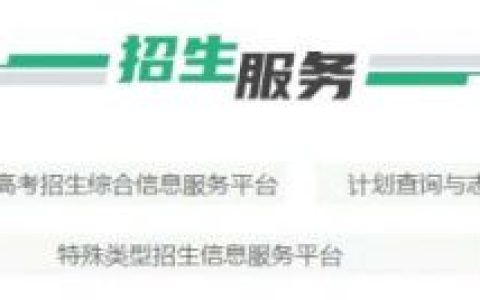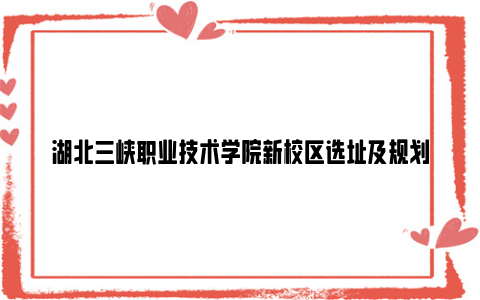在轰轰烈烈的1927年大革命时期,谢冰莹的名字和她的《从军日记》,在武汉、全国,甚至世界的许多地方,都曾享有盛誉。60多年过去了,这位老兵还被一些健在的老人怀念着。
一
谢冰莹原名鸣冈,字凤宝,又名谢彬,1906年农历9月5日出生在湖南新化县大同镇谢铎山村(现属冷水江市)的一个书香人家。父亲是前清举人,担任县立中学校长达30年;母亲思想守旧,不想让她多读书,只想她以后做个贤妻良母就够了。谢冰莹生性倔犟,为了要上学读书,竟绝食3天,迫使家人同意她进入私塾。12岁时她进入当地的大同女校,14岁远赴益阳信义女子中学,15岁考入设在长沙的湖南省立一师。在学校,她尤其喜欢文学。一次谢冰莹见一位太太让客人们品评新买的一个丫头。气愤至极,回到学校,信笔写了一篇《刹那的印象》,发表在长沙《大公报》的副刊上。
处女作的发表,使她对文学的兴趣更加浓厚,她在求学期间,又发表了《爱晚亭》、《不自由,毋宁死》等作品。然而,她母亲却一直在耳边唠叨,要她和一个早在3岁时就为她订下的、而她深信“将来决不会和他结婚的”男子完婚。正在她苦闷傍徨的时候,1926年底,设在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政治科来长沙招生,而且破天荒地要招女兵。谢冰莹在二哥的支持下,“为了想受点军事及政治的训练,将来好实际参加革命工作”,决心“投笔从戎”。初试结果,军校政治科在长沙录取女生44名,谢冰莹的名字排在其中。
二
1926年12月16日,她与同伴乘车北上武汉。经过复试,谢冰莹正式进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女兵中的一员。
不久,黄埔军校五期政治大队、炮兵大队和工兵大队1700多人亦迁来武汉,中央军校政治科遂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亦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谢冰莹被编入第六期。
初入校的那天,女兵们衣着打扮各异,三五成群地在那里叽叽喳喳,说长道短。
女兵连长在整队集合时告诉她们:“你们首先要认清楚,到这里来不是象在文学堂似的过着浪漫的、舒适的小姐生活,你们都是兵,今天开始入伍,军人的天职是服从纪律,服从长官,要整齐严肃,吃苦耐劳”,谢冰莹和女兵一样,“精神顿时振作起来”,想到“过去的一切浪漫习惯都应该去得干干净净才行”。
1927年2月12日,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宋庆龄、吴玉章、董必武等到会祝贺。代理校长邓演达在开学典礼上强调:武汉军校要继承黄埔军校传统,“使军队受党的指挥,使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并重,使革命的武力与民众结合。”“不仅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还要进而参加世界革命,谋全人类解放。”政治总教官恽代英也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到中央军校来学么事呢?都晓得说‘来学革命’。革帝国主义的命,革封建军阀的命。简言之,就是国民革命。这个艰巨的任务,要经得住苦学苦练,才担负得起来。”他们的谆谆教导,使谢冰莹热血沸腾,决心“把自己的前途和幸福,都寄托在革命事业之上。”
军校开设了帝国主义侵略史、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群众运动及群众心理、政治经济学大要、中国社会发展史、国民革命军历史及战史、苏俄研究等课程。恽代英亲自给女生队讲解工农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北伐战争形势。邓演达除讲课外,还经常在每周一次的总理纪念周上为大家作报告。女兵们回忆:“他勇往直前,朝气蓬勃,使得一般青年在工作上处处以他的精神为典范。”政治的教育,榜样的力量,大大地激励了谢冰莹。她深信,只要“举起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拳头,站到飘荡在空中的革命的旗帜之下来,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一定会成功。”她和同伴们经常走上街头,下到工厂、农村,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封建军阀的道理,动员妇女放足、剪辫并组织起来。她回忆那时的情景说:“我们嗓子叫哑了。我们脚底走起泡了,晚上只睡5个钟头。工厂里、茅棚里、学校、十字街头、汉阳门、江汉关码头……何处没有我们的足迹呢?”她还积极参加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在斗争中她看到了“伟大的、不可抵御的民众之力”。她写道:“仅仅在一点多钟内,居然把英租界收回了,……就这样轻易地由万万千千的劳动者、学生、军人、革命的老百姓,用团结的力把紧紧地被握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块地盘夺过来了,真威风啊!”
在学习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以及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军中勤务令等军事课程时,谢冰莹经常腰扎皮带,打着绑腿,在操场跌爬滚打。几个月功夫,她掌握了卧射、跪射、立射等技能和变换队形、指挥班排进攻的组织要领。
紧张而艰苦的训练,使谢冰莹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反帝反封建的女兵。
三
1927年4月中旬,由于国内外敌人的敌视和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形势陡变,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面临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4月19日,国民革命军在武昌南湖举行了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为配合北伐军的行动,军校决定在女生中挑选20人组织宣传队开往前线。谢冰莹和许多女兵争先恐后地报名,当她听到出发河南的女兵名单的第二名便是自己时,竟“喜得发狂”。临行前,她写了一封致全体女兵的信,表示已“把感情武装起来,要为国家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封信很快在女兵中传开,并为总政治部办的《革命军日报》全文刊载。她还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壮别信给当时在长沙《通俗日报》任主编的三哥,三哥见信,连忙让人发排刊登并乘车赶到武汉。谢冰莹看见三哥“声音有点颤抖,眼泪在眼眶里游泳”,连忙让他看墙上写的“革命者,不流泪,只流血”的标语,相约打了胜仗后回来痛饮。这时的谢冰莹,已将自己和革命完全融为一体,决心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切了。
当谢冰莹和其他女兵焦急地等待出发的消息时,武汉的形势急转直下。杨森趁武汉空虚之际,于5月4日发布进犯武汉的“动员令”,从万县东下,镇守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收买下,与杨森默契配合,杨、夏的突然袭击,使武汉国民政府中的汪精卫、孙科等人大惊失色,武汉市面更是谣言纷起、人心惶惶。在这严峻关头,国民政府中的国民党左派和政治学校(中央军校武汉分校3月已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的中央独立师赴纸坊迎敌。奉命出征的军校师生举行了讨伐杨、夏叛乱的誓师大会。军校政治总教官和中央独立师党代表恽代英深情地勉励大家:“现在就是要用我们的光明去冲破周围的黑暗”。当晚,侯连瀛师长、恽代英党代表率中央独立师奔赴纸坊,配合叶挺部与夏斗寅的军队激战。女生队4个队则编为宣传队和救护队,于次日上前线。此时的谢冰莹心潮激荡,充溢着“努力杀敌,凯旋归来”的革命豪情。
她所在的宣传队5月19日上午出发,下午1点多钟到达武昌县土地堂。那里刚进行了一场激战,尸横遍野,伤员甚多。师长命令宣传队派20人去当看护。特别指定要选派从前预备出发河南的同志。谢冰莹和刘光慧、王继夫、曹泽芝、刘淑召、段振亚等6人被分到刚组建的第十一军教导营。谢冰莹听说前一个晚上有许多本来可以治愈的伤员因无人救护而死去,心里十分难过。她一边救护伤员,一边暗下决心,要“踏着死者的足迹,继续伤者未完的工作,努力去与敌人奋斗”。她认为“救一同志,即杀一敌人”。因而工作特别耐心,特别负责。
叶挺部队在纸坊、土地堂大败夏斗寅叛军。5月21日攻占咸宁,接着追敌至汀泗桥、蒲圻。夏斗寅残部经鄂东南向安徽方向逃窜,武汉转危为安。中央独立师随即奉命西征,配合由林伯渠,李富春分别担任党代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六军讨伐杨森。谢冰莹也随所在部队从蒲圻到嘉鱼,渡江至新堤(今洪湖市)再至峰口。直到革命军收复长沙、宜昌。杨森叛军分水陆两路向巴东、万县方向撤退后,才班师回汉。
这40多天的工作和生活,对谢冰莹和与她同时代的人来说都是传奇式的。她第一次看到遍野的尸体和哀号的伤员;第一次了解到封建军阀的残暴和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支持;第一次认识到必须建立工农和学生武装,才能推进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
到咸宁后,她除救护伤员外,经常抽空协助作妇女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她深切地感到“我们是有主义的军队,我们是百姓的军队,我们到一处受一处民众的欢迎。”可惜没有亲自上前线冲锋陷阵,“尝尝枪林弹雨中生活的滋味”,她为此深感遗憾,因而在抢救、护理伤员时尽心尽力。她随身所带的毯子、水瓶、包袱以及日记等一开始便在路上丢失了,“饷及一切东西都没有发”,结果只剩下一身军衣,洗澡、发信、喝茶、买零用东西的钱,“一概是借着别人或者是随便用同志们的”。结果,女兵们都成为“除了扣子没有铜”的穷光蛋。但她们没有因此而气馁。
在从峰口回新堤的船上,她们自己划桨,自己撑篙,十分兴奋地听着战士们唱着Intemational(《国际歌》)和“青的山,绿的水,灿烂的山河;美的衣,鲜的食,玲珑的楼阁;谁的功,谁的力,劳动的结果。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呵!”的曲调。
饥饿,疲劳,死的威胁,统统都没有难倒充满革命激情的女兵们。几十天“又艰苦又悲壮,同时又很有趣味的行军生活”,“有意义,有价值,雄壮,痛快”,使谢冰莹从身体到精神境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无限感慨地写道:“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我忘记了自己是个女人。从未想到个人的事,我只希望把生命献给革命,只要把军阀打倒了,全国民众的痛苦都可以解除,我只希望跑到战场上去流血,再也不愿为着自身的什么婚姻而流泪叹息了。”
四
自从在长沙《大公报》发表了《刹那的印象》后,谢冰莹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到了军校,她先后在军校办的《革命生活》日刊上发表了几篇作品。由于酷爱文学,她的朋友冰川引荐她认识了孙伏园、林语堂两位当时武汉的文坛巨匠。孙、林两位十分器重她的才气,她也“暗中拜他们为老师”。参加讨伐杨、夏的战斗时,她已抱定了牺牲的决心,极力想写出自己所见所闻和所想的一切,写出这个“悲壮伟大”的时代,让人们了解当时青年们特别是妇女们的心态。行军途中,当然没有宁静的书房和宽大的书桌,只能用各种间隙,随便找个地方,靠着膝盖、信笔写上几句。“只管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看见什么就写什么。”她所写的文字先命名《从军日记》,以后改为《随意记》。她把所写的一切都寄给孙伏园和林语堂,让他们了解“前方的士气和民众的革命热情,是怎样的如火如荼”,同时也要他们替她保存,但她并没想到发表,更没想到会出书。
孙伏园和林语堂收到她陆续寄来的日记和散记后,十分高兴。正像林语堂事后评价的那样,“我们读到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年轻女子,身穿军装,足着草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拿一支自来水笔,靠着膝上振臂直书,不暇改窜。戎马倥偬,束装待发的情景;或是听见在洞庭湖上,笑声与河流相和应,在远地军歌及近旁鼾睡声中,一位蓬头垢面的女兵,手不停笔,锋发韵流地写叙她的感触。”谢冰莹的日记和散记朴实无华,是未经雕琢的最自然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那个伟大时代里青年的爱国牺牲精神和当时人民的苦难以及拥护革命的热情,孙伏园便把它们在他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公开发表。从1927年5月24日起刊出第一篇日记,至6月22日止,刊出最后一篇散记。
《从军日记》的发表,立刻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震动了当时的文坛。林语堂还把它译成英文,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连载。许多人向孙伏园、林语堂打听谢冰莹的情况。武汉国民政府负责人之一的谭延闿也向孙伏园了解谢冰莹。美国一个报纸主笔在读到英文本的日记后,特别函请《中央日报》多登这类文章。于是林语堂把所有的日记、散记都译成英文,交商务印书馆设计绘制,出版不到一个月,一万册很快卖光,于是再版、三版一直到十九版。汪德耀先生接着又把《从军日记》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读到后,特别致函谢冰莹表示祝贺。谢冰莹一时成为中国广大群众和世界文坛所注目的人物。
但谢冰莹并不因此而陶醉,她始终认为那是一部幼稚的,谈不上结构、修辞和文章技巧的作品。在她已成名的几十年后,仍然谦逊地说:“我绝不承认我有什么写作天才,我是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也是个脑筋最简单的人……如果问我有什么特点,那就是能吃苦,不怕劳,不论做什么事,但顾耕耘,不问收获;不肯向现实低头,有跌倒了爬起来,失败了再干的勇气。……假如不是参加北伐,我不会了解社会如此复杂,民间如此疾苦,革命如此重要;诚实的民众和热情的男女青年是这么可爱的。”“没有伟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是不能写出好作品来的。”
五
当谢冰莹等女生队员身心凯旋回汉后,湖北省妇女协会为她们开了祝捷会,并送了一面题有“开历史新纪元”字样的锦旗。
此时,国民政府中汪精卫一伙,正积极酝酿反共;武汉军校被他们称为“赤子赤孙”的摇篮,亟欲扼杀而后快。为保存革命力量。恽代英将军校的女生队员作了妥善的安排。谢冰莹象做了一场大梦一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湖南。
这以后她的生活极其苦涩、艰辛而又富有传奇色彩。她母亲强迫她尽快出嫁,她连续3次私逃,又3次被抓回。最后只得扮演了一场傀儡戏的主角,到了婆家,然后说服了那个名义上的丈夫。借应聘任教的机会,一举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枷锁。她从长沙到汉口、上海、北京、东京、厦门,进过上海艺大和北京女师大,当过小学和中学教员,编过报纸副刊,但始终没能摆脱穷困潦倒的境遇。几次被误捕入狱,差点送了性命;她几次被列入黑名单,遭通缉追捕。
1936年4月,她到日本,因拒绝去欢迎到东京来的伪满皇帝溥仪,被送进日本监狱,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折磨。她也曾和军校时期的战友、湖北仙桃人符号组织了家庭,生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但因一些误会,终于感情破裂,各奔东西。所有这些挫折和打击,都没有使她气馁,只是使她认识到“社会太残酷了”,她奋力抗争着,并写出了一些颇有影响的新作品。1937年“七七”事变后,正在长沙养病的谢冰莹毅然组织了“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率领一批妇女和青年学生,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奔赴淞沪前线。在救护伤兵、发动群众的同时,重新用那生花妙笔描写出中国军民可歌可泣的抗战场面。1938年4月她来到武汉,多次到各单位、团体作“前线归来”的演讲。4月14日的汉口《新华日报》曾刊登广告说:“冰莹女士的《从军日记》记北伐参战经过,曾得到广大读者的称誉。‘八一三’以来,冰莹女士又参加抗日前线,将其战场生活,写成新从军日记一册。都十万余言,并附战地照片多幅。在本书中可以见到新中国新女性活跃的姿态,可以见到前方将士在枪林弹雨中与敌人肉搏的情形,书已付印,不日出版。”
1939年4月,谢冰莹来到湖北宜昌开办战地服务训练团。培训战地服务和医疗人员。后来,在日机轮番轰炸宜昌,训练团的驻地被炸,她立即决定把提前毕业的学员分配到从宜昌到十里铺的12个伤兵招待所,救护伤兵。在宜昌,她与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畅谈过中国的神圣抗战,会见过日本反战人士,并与朝鲜义勇队员联欢。还和武汉军校时的战友、当时在第五战区从事抗日文化工作的臧克家共忆北伐时的峥嵘岁月,探讨神圣抗战的前途。由于过度劳累,她病倒了,并动了手术。但稍事休养后,又投入到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她从成都经重庆、武汉回了一趟湖南老家。不久到武汉任《和平日报》和《华中月报》的副刊主编。同时抱病写作《女兵自传》的中卷,并以《女兵十年》的书名在上海北新书局和北平红蓝出版社两地出版。林语堂的两位女儿还将它译成英文,由林语堂亲自校正并作序,在美国的John Day公司出版,译名为《Girl Rebel》。后应母校北平师大之邀,赴乎讲授“新文艺习作”,并兼任《黄河》月刊主编。1948年谢冰莹去台湾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前身)任教授,讲授国文和“新文艺习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陆陆续发表了一些怀念、介绍和研究谢冰莹的文章。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女兵列传》将她的传记和宋庆龄、何香凝、向警予、蔡畅、邓颖超等人的传记并列。她的战友、前夫符号在武汉军校同学的一次聚会上赋诗怀念、殷切希望她回归。但谢冰莹因年老多病,不堪旅途劳顿,始终未能成行。
她在一篇题为《还乡梦》的结尾写道:“这究竟是梦还是现实呢?也许是一个真实的梦,不管它是梦还是现实,我都愿意回去,永远投在故乡的怀抱,嗅着泥土的芬芳。可爱的故乡呀,我永远记着你四季如春的风光!”
原创文章,作者:nbdnews,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nbdnews.cn/06/14/47/293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