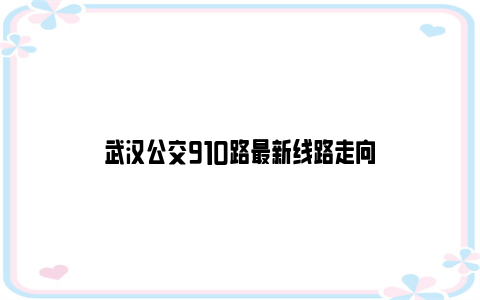汉阳临嶂山距笔者出生地蔡甸小镇2.5千米。日军侵华武汉沦陷之时,吾辈辍学少年常常结伴游览临嶂山山腰之古城遗址。
匆匆岁月如流。1990年笔者离休,往昔少年好友,也是当年临嶂山玩伴叶华运先生(曾任汉阳县农机局书记),赠送我1988年新编《汉阳县志》一本,得之如获至宝,竟日阅读浏览。该县志记载:“(临嶂古城)原城址尚有六七米残存。”因此笔者特意于2004年到临嶂山一游,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山上根本无有残存的古城遗迹,仅见一座“武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水泥碑,无奈地伫立在残破的山坡,人们仍然毫无顾忌地开山采石不止,开山采石曝破的飞石,险些击中我们乘坐的车辆。悻悻返回后,撰写了拙文一篇《临嶂山忆旧》,刊载于《长江日报·城周刊》。
光阴似箭,转瞬间,距上次重游临嶂山,又是八年,随着经济发展及城镇化进程,一座座摩天大楼相继耸立,我以为临嶂山由于开山采石,已经夷为平地。
然而,日前偕同友人及家人郊游,在石榴红村的汉江堤岸,无意间发现了彼岸的“临嶂残岩”。欣悦不己,于是偕同家人又重游了一回临嶂山。八十耄耋老翁,深恐人们遗忘临嶂古城及其历史,特撰文《临嶂山拾掇》,以飨读者。
临嶂山怀古
“幡冢导漾,东流为汉。”长江最大的支流,古老的汉水,流经峡谷和原野来到这里,即将汇入长江。它曾经波涛汹涌,猛烈冲击临嶂赤壁,掀起滔滔白浪。而今因为它的上游有了丹江水库,所以它静如处子,默默地从我们对岸的临嶂残岩,流淌东去。
因陈寿著《三国志》及相关史书,对赤壁大战的具体地理位置没有记载,所以湖北省境内,竟有黄州、武昌、嘉鱼、汉阳、汉川多处赤壁之争。也有前人据盛弘之撰《荆州记》“临嶂山南峰,谓之乌林峰,亦谓之赤壁”,而认定临嶂赤壁即赤壁大战之地。
吾辈少年时所见,往昔临嶂山赤壁巍巍屹立江滨,峻峭如屏,似由仙人神刀所削。滚滚江流,碰撞山岩,湍急左折,形成回旋,是当年我们蔡甸人乘小木船“下汉口”必经的一处险境。
距今1690余年,这里就有一座城池。中国最早的地理名著,北魏郦道元(466或472—527)撰著《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记载:“沔水又东,迳临嶂故城北,晋建兴二年(314年),太尉陶侃为荆州,镇此。”这是关于临嶂城最早的记载。既称“故城”,其建城年代,将会更加遥远。
唐李吉甫(758—814)撰《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七》:“沔州·汉阳上:本汉安陆县地,晋于今州西临嶂山下置沌阳县,江夏县自上昶城移理焉。后郡又移理夏口,沌阳县属郡下不改。入陈废。隋开皇置戍,十七年废戍,改置汉津县,属沔阳郡。大业二年,改为汉阳县。武德四年,分沔阳郡于汉阳县,置沔州及县,并自临嶂山下改移于今理。”
《元和郡县图志》写成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这里所谓“改移于今理”,应是唐武德四年(621年)后的汉阳县治,凤凰山南麓的汉阳古城,即今汉阳区凤凰山南,鹦鹉花园小区以北,显正街与西大街连接处(老居民称西门),向东至江边的地段。
从晋建兴二年到唐武德四年,临嶂城作为沌阳县治、安陆县治、江夏郡治达307年。
又经历477年,到宋崇宁七年(1108年)金人入寇,宋朝廷徙德安府治临嶂山。明《嘉靖汉阳府志》有3段记载:
崇宁七年(1108),徙德安府治临嶂山。”(《府志》刻本有误,宋崇宁年号共计只有5年,按推算,应是大观二年。)
(绍兴)四年五月,以岳飞兼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
七月,岳飞使王贵、张宪复邓、唐州、信阳军,襄汉悉平,飞移师次德安,军声大振,是时府治在临嶂山,军属府。
史称岳飞收复襄阳六郡之战,宋史记载:“飞渡江中流,顾幕属曰:‘飞不擒贼,不涉此江’”。即此战前。
这史实记载说明,岳飞曾率领大军驻扎临嶂城,这里不仅是防守金人入侵的城堡,也是宋军北伐的基地。
汉阳临嶂山,是我们的先民繁衍生息的地方,也是他们撕杀搏斗的战场。它是我们这座城市的过去,记住它,才能更加感悟到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生活的甜美。
临嶂故城遗址存疑
迄今所存可阅古籍都记载:沌阳县治及临嶂城,在临嶂山下。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七·沔州汉阳上》记载:“晋于今州西临嶂山下置沌阳县。”又记:“武德四年,分沔阳郡于汉阳县,置沔州及县,并自临嶂山下改移于今理。”
而我辈童年嬉戏少年游览所见,临嶂古城遗址残存而完整的城垣却在临嶂山腰。1988年新编《汉阳县志》也记载为“此城建于山腰,绕山而筑”。既在山腰,应称山上。
笔者认为:1.《元和郡县图志》是唐朝地理名著,是我国现存最早又较完整的地方总志。2.其著者,唐李吉甫生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逝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李吉甫在世时间距武德四年汉阳县治从临嶂故城改移凤凰山,仅约一百三四十年。3.既然到北宋徽宗赵佶的崇宁年间“徙德安府治临嶂山,”则可证明从唐到宋,虽然临嶂城不再是县治所在,但其城址犹存。4.一字千虑的史家笔下,不会误用一个“下”字。5.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也记载:“东晋于临嶂山下置沌阳县,后废。”
因此笔者判定:宋以前“临嶂故城”当在临嶂山下。
到了明朝,嘉靖《汉阳府志》才有:“沌阳废县:在县治西六十里,临嶂山上。”的记载。但该《府志》又同时记载:“宋咸宁七年,(宋无咸宁年号,《府志》刻本有误,应为崇宁七年)德安府迁治于此,筑城守之,故又以临嶂为城头山。尚存城基。”这段记载给了我们3个信息:一是金人入侵,德安府迁治于临嶂山。二是“筑城守之”,显然没有利用原来的城池,而是新筑城堡守之。三是“故又以临嶂为城头山”,城头山之名,始于宋迁德安府治于临嶂山。
笔者追忆,吾辈童年嬉戏,少年游览之“临嶂古城”遗址:确在临嶂山腰,与1988年汉阳县地方志办公室编纂出版的《汉阳县志》所记相同。绕山而筑,遗址略与临嶂山等长,但其深度不足10余丈,历历可辨岩石堆砌的城垣城壕,而未见街市及屋宇遗迹,从山下到遗址又无大路可攀,更无官道,分明是一座战时的城堡,而非居有平民的城池。
笔者在《临嶂山忆旧》文中曾描述:“远眺临嶂山,清晰可见临嶂山山脊,宛如连连的城垛……”笔者坦言,限于当年吾辈游伴们的年龄,我辈确实没有攀上临嶂山山脊,但近看那一个个的城垛,四方整齐,绝非天然形成,而是由人力凿削堆砌而成,是用作瞭望、指挥、发射弩矢的战争建筑。
笔者的结论是:笔者少年游览所见,1988年编纂出版的《汉阳县志》所记,即是“宋崇宁七年,德安府迁治于址,筑城守之,故又以临嶂为城头山”中新建之临嶂城堡。
然而,德安府迁治临嶂山时,“临嶂故城”还存在吗?临嶂山下之“临嶂故城”在那里呢?
“废城”是否古城遗址
旧时汉阳城头山(临嶂山)上,宋朝新修建之临嶂城堡,仅具有战守的功能,尤其针对金人的骑兵,它实际上是一道坚固的防线。
那么迁移到此处的德安府治官署及其随同南迁的平民在哪里呢?《宋史·岳飞传》与嘉靖《汉阳府志》皆记载;岳飞为“德安府制置使”,“飞移师次德安”,而岳飞所率领大军食宿及生活供给怎样解决呢?因此这道防线即城堡的后面,一定有个后勤基地。那就是古籍上所记载的临嶂山下的临嶂故城。
临嶂山北,是面对来犯之敌的坚固防线。临嶂山南,山脚下就应该是临嶂故城。
寻常百姓祖祖辈辈口口相传事,“史书所不屑”。我们蔡甸的老祖母们、老母亲们告诉我:临嶂山南,汉水之滨,有一个地方,叫“废城”,那可能就是临嶂故城。
日军侵华武汉沦陷时期。日军对我农村及新四军控制地区实行食盐禁运及经济封锁,于是蔡甸镇上就诞生了一批“跑生意”的妇女。所谓“跑生意”,实际上是一群打破日军经济封锁,可敬的“走私人”。她们头天乘小木船“下汉口”,一般在万安巷码头起坡,汉正街进货,明的是经营火柴、牙膏、牙刷、肥皂等小百货,暗中夹带食盐、香烟,次日乘小木船,设法瞒过日军设在水厂的水陆联合检查站,返回蔡甸售卖。
除水厂水陆联合检查站外,日军还在汉阳十里铺、升官渡设有检查站。沦陷初期,在“废城”还有个不明武装分子设立的“厘金站”。他们是游击队还是土匪分辨不清,一般他们在早上出现,拦截下水(行)的船只,由船老板代交厘金,事后乘客分摊。也有“跑生意”的,返回蔡甸途中,在“废城”遇上他们,所带货物被洗劫一空。所以跑生意的人,带着货物返回蔡甸,经过“废城”都要叮嘱船家,“废城快到了,船老板!靠北岸,快点划”。
这篇文章写到此,就要搁笔了。但是在我的耳边,缭绕着那浓重的蔡甸腔,亲切的乡音“废城!”“废城!”不绝入耳。
原创文章,作者:nbdnews,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nbdnews.cn/10/09/41/29768.html